伍国:中国人才在美国成功算哪边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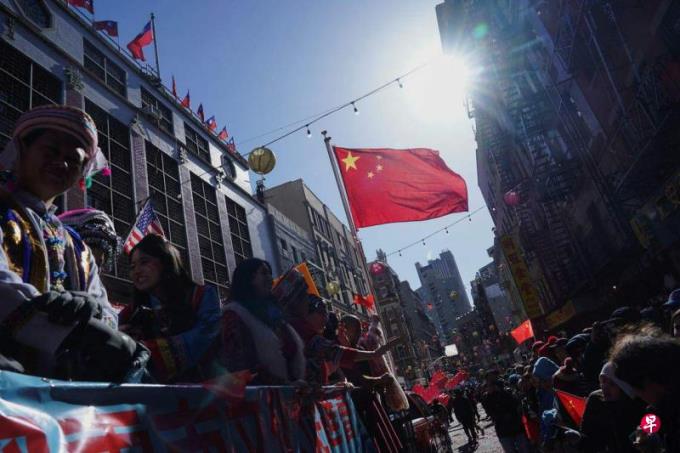
笔者认为,华人在美国的“人才”,无一例外受益于中国的社会经历、教育背景、阅读经验,以及长期的回忆和反思。美国肯定拥有更包容的制度和心态,但在这个权力场域中,外来者的适应和博弈,可能比简单化的“成功故事”更为复杂。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疑问:美国的华人人才,有多少是在中国成才以后去美国的,有多少是在美国完成学业以后成为人才的。这个很有趣也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涉及几个层面的关注:第一,是否存在中国人才在国内默默无闻甚至受过针对,到了美国大放异彩这个现象;第二,由此进一步,是不是因为美国提供了更包容和更有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来到美国后更能人尽其才而不被埋没?第三,这里的“成才”和“人才”的定义和标准又是什么?特别是在人才流动日趋频繁,一个人往往兼具多重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到底算哪边的,就像外包加工后卖回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出口商品,究竟算产于哪里一样,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这似乎也涉及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引起广泛兴趣的“人才学”问题。一个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靠少数杰出人才推动,惠及一般大众的。因此,那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歌颂泛政治化和千篇一律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开始变得多元化。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人才”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意义,不是去制造千人一面的英雄模范,而是在新兴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标准下,注重一个人的某些个人才能和特殊的专业贡献,并包容某些个体缺陷。在这一价值转换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舆论,曾推崇过数学家陈景润这样非政治、纯学术,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缺少自理能力的世外高人,后来也关注和歌颂过一批大刀阔斧推行企业改革,或最早承包国有企业的个性鲜明的改革家型人才。
这样看来,人才就是拥有某种专长和才干,能把所长发挥到极致,拥有鲜明个性,甚至会引起社会争议的一些人物。这种形象比无可争辩的高大全型旧式“英雄模范”多了个人特质和色彩,贡献也不限于道德感召,而是对社会变革或学术研究更切实的推进,同时帮助大众初步认识到价值多元的意义,引受众深层思考。比如,女明星刘晓庆的绝对自信,女作家遇罗锦对自我感受的追求,都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婚姻模式。
然而,对同一社会旧有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旧制度的挑战,在跨国背景下,又呈现不同的样态。对于离开母国的人来说,适应异国强势的主流文化是一个须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跨国“人才”来说,可能很长时间,或许终其一生,都是处在一个适应和学习,而不是挑战和重构的过程中。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影响至深
回到最初的问题,应该说,多数在美国科技界和学术界取得成就的华人——这里特指在成年后通过留学和移民定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其根本世界观、价值观、情感或说在纯粹专业以外但更根本推动他们成功的一些隐形因素,一定是在出国以前就已经奠定的。更简单地说,这些“人才”在被美国的高教和科研制度最后可见地“培养”之前,已经具备成功的基本条件和潜力,而且有的人已经做出初步贡献。在这些到达美国之前的条件中,包括一个重要而常被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
从老一辈已故美国华裔社科学者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不论是何炳棣、余英时、唐德刚还是林毓生、张灏,或者尚健在且活跃在学界的黄宗智,全部出身于晚清到民国时期条件优越的经济和文化精英家庭。他们的精神底色以及一生的学术志趣,早就被家族以及亲身经历过一部分的动荡的中国现代史,乃至中国人之间的师承关系(如萧公权之于黄宗智,雷海宗之于何炳棣,钱穆之于余英时,殷海光之于林毓生和张灏,乃至文学史大家夏志清和夏济安兄弟之间的相互扶持)所形塑。
美国所提供的,是更加规范化的现代学术训练,前沿的研究理论和范式,世俗化的名校光环,和在学术界立足的英文出版和研究环境。但正像在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史六十年》中看到的,他虽然也感谢美国导师对自己博士论文的赏识和肯定,但真正富有感情地以名字为小节列出来单独追忆的人,全部都是在中国求学时的师长,从郑天挺到冯友兰,名字达九人之多。他没有单列一个美国教授来长篇回忆,在美国教学几十年,回忆录中竟没有提到一个美国学生。
在笔者更熟悉的中国大陆旅美历史学者群体中,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者,在赴美求学之前已经在中国完成研究生教育,甚至很多人已经在大学任教,出版过专著,然后才出国深造。这部分学者在赴美之前已经在精神上成熟,家学渊源、学术传承,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亲身体验和相当多的个人创痛、奋斗和挣扎,同样深深植根于意识深处。
美国式的博士教育、学术研究路数、创新法门,乃至学术出版体系的窍门,只是嫁接在前半生的中国经验根基之上,使其再塑金身。可以说他们是实现了自我的提升、眼界的拓展和学术境界的升华,但不能说是到了美国“才”成为“人才”。即以美国人天天津津乐道的批判性思维而言,假如不是已经具备足够的批判性思维,一个中国的大学教师何必克服重重困难远赴异国留学?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由于第一代移民很多时间是在文化震撼中观察、学习、模仿、融入,这也导致留美学人几乎很难在研究上取得突破性创获,而往往是在美国人已建立的范式当中,或自己的导师已建立的研究先例之后,进一步找到中国例证,进行在技术上十分细致的实证研究。也因为模仿和融入的漫长,这个学者群体没有正式地书面参与过一次英文学界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论争,不论是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黄宗智则作为非大陆背景的更老一辈学人参与)的论辩,还是前几年沸沸扬扬的“新清史”之争,但又还停留在是否被美国主流学界在大型会议上“看到”的焦虑中。
世俗意义的成功掩盖很多问题
笔者想指出的是,中国学术人才在美国世俗意义上的可见的成功,包括取得名校学位,获得终身教职,出版专著,可能掩盖了很多被忽略的问题,包括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不参与重大问题论争,以及和美国学生之间难以取得师生“教学相长”的默契的促进,也很难实现很多中国学者心中的“学术传承”这一理想等问题。确实,大多数哪怕学术成果一流的华裔学者,也常受困于美国三流学校,这在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里早就说得非常清楚。
在普通的美国大学里,华裔教授常常花费大量精力思考如何得到学生的较高评分,如何试图弥合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两种社会的生活经历,并有专业社科研究经验的“中国”学者,和大量来自美国内陆,经历简单,而且世界观受到美国商业媒体严重影响的学生之间的背景与认知鸿沟。这样的弥合和普及,澄清式的“解释”诚然是必要的,也是做教师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仅是一个传播问题,很难说是纯学术意义上的高质量交流和精神上的高质量共鸣。
也许正因如此,一名在中英双语中成就卓著的“50后”美国华裔学者曾向笔者坦承,他希望把毕生所学“传承”给他兼职教学的中国研究生。笔者也始终认为,另一位背景强大、学力深厚的已故前辈学者,“假如”在中国一流名校任教,应该比在美国能影响更多学生,更可能成为相关领域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而也正是这位学者后来认识到,华裔学者应该具有更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不能一直做一味适应美国范式的人。
近期因为浙江大学解职、辞职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在笔者看来同属在个性上或许不完美,但经历、问题意识、责任感还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华裔高级学术人才。赵教授之所以在美国荣休以后心心念念回中国,按自己方式和经验来加强和改造一个社会学系,培养中国学生,还是有着属于他那代人的某种中国情结和理想主义因子。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笔者认为,华人在美国的“人才”,无一例外受益于中国的社会经历、教育背景、阅读经验,以及长期的回忆和反思。事实上,即使是以英文创造性写作成名的作家如哈金、李翊云、严歌苓,也是在写中国,写自己;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就不是一个俄罗斯的故事,只有在其回忆录《说吧记忆》中,我们才看到那个在记忆深处的俄罗斯。
当然,在思维、创作和价值观上如何突破“中国瓶子”,是另一个议题。其次,有在中国不如意的人在美国更成功,也有在美国过得不怎么样的美国人,在中国觉得如鱼得水,这可能和个体际遇有关。第三,美国肯定拥有更包容的制度和心态,才能容许大量移民尽可能发挥所长,为美国所用。但是在这个权力场域中,外来者的适应和博弈,可能比简单化的“成功故事”更为复杂。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